
康斯坦丁·布朗兹,1965年4月生人,俄罗斯动画导演、编剧,代表作有《山顶小屋咚咚摇》、《便所爱情故事》、《离开宇宙我们无法生存》等,凭借《便所爱情故事》、《离开宇宙我们无法生存》两次入围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提名。《山顶小屋咚咚摇》被昂西动画电影节评为“动画的世纪·百部经典”之一。
ASIFA国际动画协会在第16届厦门国际动漫节“金海豚”奖的评审期间对康斯坦丁·布朗兹先生进行了深度采访。
A:我在童年就深深地爱上了动画。在我大概6、7岁的时候,苏联电视台播放了美国的动画系列片Mighty Mouse(中文译为《太空飞鼠》或《大力鼠》),你们太年轻可能不知道这部片子,千万不要把Mighty Mouse和Micky Mouse混为一谈,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动画作品。
Mighty Mouse是特里工作室(Terrytoons)自1942年开始制作的电视动画系列片,主角是一只和超人一样的超级老鼠;该片从50年代一直播到80年代,影响深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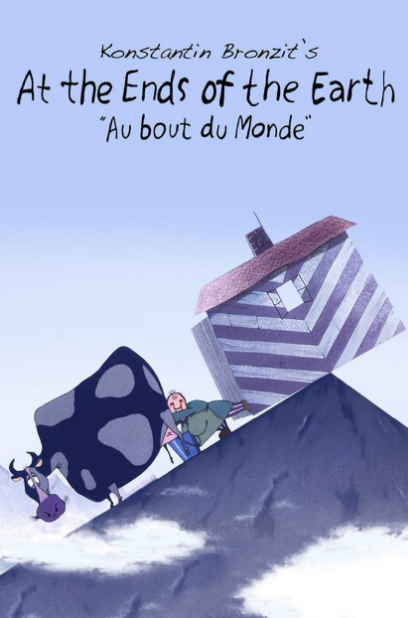
《山顶小屋咚咚摇》(At the Ends of the Earth)海报
顺便说一下,《山顶小屋咚咚摇》并不是我首次运用一镜到底的方式,我在1994年创作《开关》(Switchcraft)的时候就进行了一镜到底的尝试,这次尝试让我知道一镜到底并非不可能,这也是一种创作方法。

《开关》(Switchcraft)截图

《神》(The God)海报
除此之外,我当时所在的Melnitsa工作室完全没有三维动画的制作经验,只有一个自学三维软件的小伙子勉强能做。但当我看到他做的模型动态测试时,我简直想自杀——太丑了!丑的离谱!离我头脑中的设想相去甚远。我觉得以当时小伙子的水平,可能根本无法实现我的构想。
 Melnitsa工作室成立于1999年,是俄罗斯最大的动画公司
Melnitsa工作室成立于1999年,是俄罗斯最大的动画公司
A: 说实话,若我声称我不在意结果未免显得太虚伪了——既然不在意,又何必去报送参赛?但我可以接受失败,任何竞赛都必须做好失败的准备,用拳击界的术语来说,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职业素养——承受重击的能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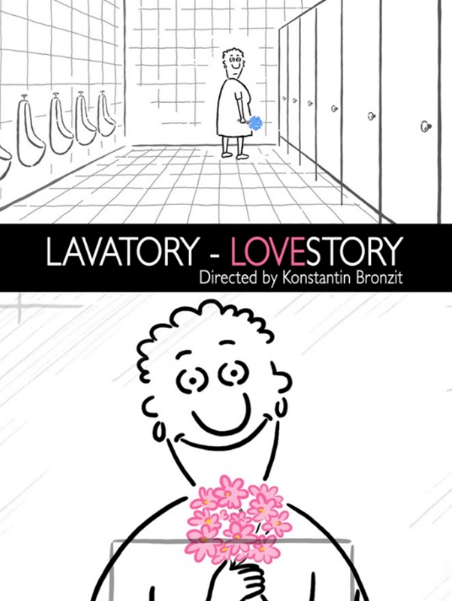
《便所爱情故事》(Lavatory-Lovestory)海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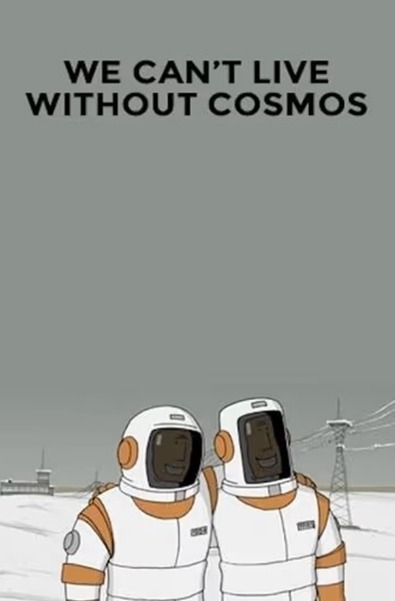
《离开宇宙我们无法生存》(We Can't Live without Cosmos)海报
现在,我们再看看,这些年我一直在创作,并有优秀作品产出(例如2019年创作的《离开宇宙他无法生存》),而那些靠着首作“一击即中”的获奖者们哪里去了?如果把奥斯卡视为电影节最高荣誉,难道不该是历经沉淀才能获得的成就吗?

《离开宇宙他无法生存》(He Can't Live without Cosmos)截图
艺术评选不同于体育竞赛,评判标准模糊而主观,使得这份殊荣可能仅凭运气就能斩获。更值得深思的是,学院派将大奖授予新人导演的首作,某种程度上或许是一种伤害——当光环来的太早,创作者往往因惧怕搞砸而难以投入新的项目,这种心理枷锁比任何批评都更具毁灭性。
顺便说一句,刚才我提到的两个动画导演只是冰山一角——奥斯卡历史上昙花一现的获奖者实在不胜枚举。想到这一点就让人扼腕:像马克·贝克和乔安娜·奎因这样世界级的动画大师,至今未能捧回属于他们的小金人。因为评委们只会就片论片,而优秀作品往往难分伯仲,最终评判难免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。
Q:您在平时是怎么积累创作灵感的?
A:我从来不会去积累灵感、寻找灵感,不会“憋”出一个故事。有时,我的内心会受到一种从天而降的信号冲击——这可能就是你所谓的“灵感”。每当新想法出现时,我其实很痛苦,他就像雷德利·斯科特的《异形》,剧情扎根在脑海中,不断自我生长,因为你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它。它毒害了我的生活,剥夺了我的平静。而摆脱它的唯一方式,就是将它以动画的形式释放出来。
但我并非一开始就有这种感觉。年轻的时候,当我刚完成《山顶小屋咚咚摇》,一个关于印度神祇的故事已经在脑海中盘旋了,那时的我很享受这种状态。而如今,每当我完成一部影片,脑中一片空白的状态才让我感觉到快乐,因为我是自由的,没有任何东西困扰我。
顺便说一句,我曾读到塔可夫斯基说过:“如果一个导演手头没有10个随时可以开拍的剧本,那他就不是真正的导演。”按照塔可夫斯基的标准,我根本算不上导演。
Q:在您的作品中,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,都能感受到一种来自“骨子里”的幽默,请问您是如何理解“幽默”的?
A: 幽默,从某种角度来说,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。这就像一个人要么有幽默感,要么没有。但另一方面,尽管不同国家的人们思维方式各异,我们却常常能对同一个笑话会心一笑。这说明幽默其实是一种国际通用语言。然而在当今动画界,真正有趣的作品实在太少了,因为创作幽默太难了。相比之下,创作阴郁风格的作品要比创作幽默的作品容易得多。
从小时候起,我就特别喜欢查理·卓别林的电影,他的幽默能被世界上大多数人所理解。他懂得如何在悲剧与荒诞之间取得平衡——这正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——即便处理最深刻的悲剧时,也必须为滑稽元素留出空间,因为真正的生活就是这样的。

Q:您所在的Melnitsa工作室创作了很多动画电影,但这些动画电影都是在本土上映,我们想知道这些动画电影为什么没有全球发行。
A: 显然,Melnitsa动画工作室是一家俄罗斯公司。因此当我们制作电视剧或动画长片时,这些作品首先会在俄罗斯本土影院上映。据我所知,发行方目前也正在尽可能地将它们推广到其他国家——包括哈萨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、阿塞拜疆、亚美尼亚等国家。我想中国和印度应该也能看到。也就是说,我们的作品有希望能在与我们最邻近的海外国家被观众看到。
Q:我们想知道Melnitsa工作室是如何赚钱的。
A:一方面,俄罗斯政府会提供一些支持。通常,所有制片厂都会将自己的项目提交给文化部申请资助。而文化部下属的专业评审委员会将决定具体项目的预算分配金额——这本质上是一场公共资金的竞逐。以文化部以及另一家机构"电影基金会"为代表的国家机构,既会资助像《离开宇宙我们无法生存》这样的独立电影,也会拨款支持面向大众市场的商业剧情片。这些资金同样会扶持青年动画创作者和首作电影。当然,预算终究是有限的。这笔资金规模不大,并非所有提案者都能获得资助,但机会始终存在。
对于Melnitsa工作室来说,更重要的收入来源还是票房,如果某部剧情片票房成功,就能为制片厂带来收益。
采访的三个小时意犹未尽,我们也问了动画迷们最为关心的问题——康斯坦丁先生目前的动画项目。
他告诉我们,他现在处于空档期,虽然脑海中偶尔也会冒出一些零散的创作灵感,但这些灵感并没有让康斯坦丁先生感到焦虑,他表示现在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停下动画创作的脚步。
虽然我们能感受到康斯坦丁先生休假的快乐,但作为他的影迷,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空档期能短一些,期待早日能看到他的新作。


